本栏目继续带您走进《上海医生在摩洛哥》,聆听50年来中国医疗队在摩洛哥救死扶伤的动人篇章。第二期特邀嘉宾是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严伟。作为第5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塔扎分队的成员,他的经历是中外友好的生动见证。下面,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讲述,感受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
最好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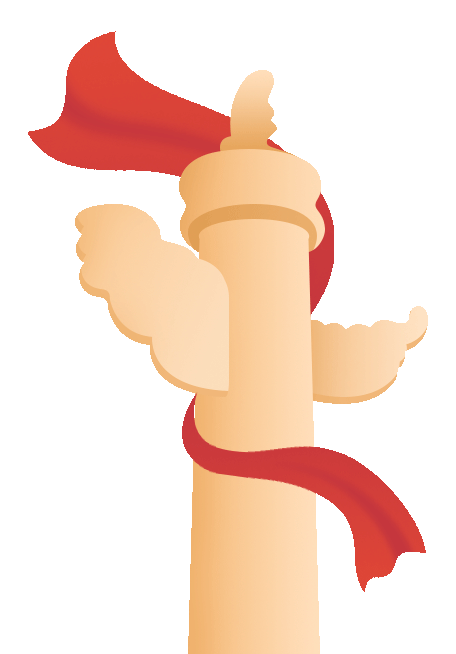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前不久,朋友给我转发了一条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中摩产科医生的使命接力: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里面写到一位摩洛哥的产科大夫伊曼,她回忆做医生的初衷,是因为自己出生时的经历,文章中写到:
1981年,伊曼的母亲在外出途中突然破水临产。紧急情况下,她赶到最近的塔扎医院,那里有一支中国医疗队驻扎。值班的中国医生诊断是巨大儿和面先露导致的胎儿窘迫,需要立刻进行剖宫产。
“那时,我的心跳非常微弱,母亲的情况也很糟糕。是经验丰富的中国医生为我母亲做了剖宫产手术,挽救了母亲和我的生命,”伊曼说,“如果塔扎医院没有中国医生,如果没有他们丰富的急症处理经验,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不会成为医生。”
朋友知道我曾经去摩洛哥两年,她问我这个值班的中国医生是否就是我,是否还记得给伊曼做手术的事。第194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总队长范晓盛也在寻找这位“中国医生”。
这篇报道唤醒了我44年前的记忆。
1981年,经过组织的层层选拔,我们一行13人从北京出发,途径巴黎飞抵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随后又乘坐大巴车辗转,终于抵达远在上海一万多公里外的塔扎。
我们是第一批到塔扎的中国医疗队,所以,报道中伊曼提及的中国医生,的确是我和我的同事——事实上,我们也是当地医院仅有的妇产科医生,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几乎所有手术都是我们俩共同完成,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连轴转,连休息日都没有。
但关于伊曼母亲的这个案例,我回想了好一会儿,还是没能从记忆中找到相关的碎片,实在是因为巨大儿和面先露这样胎位不正导致剖宫产的病人太常见了。
也许大家很难想象,毕竟80年代的上海,孕产妇们的医疗条件已经十分不错了,市一碰到最多的问题是一床难求,需要在走廊加床。但塔扎甚至整个摩洛哥,这里孕产妇没有孕检的习惯,甚至很多都是在家里分娩,分娩后因为大出血或者产后感染送医的病人很多,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这样的病人。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分娩后胎盘滞留,她把脐带绕在大腿上三天,感染已经非常严重了才用担架送过来(在上海,胎盘滞留超过半个小时已经需要紧急干预);还有一个产妇难产,送过来的时候孩子的手已经在外面了,我们赶紧剖宫产,同时还要给婴儿的小手做好消毒避免感染,再从腹部拿出来;还有孕产妇因为连着几胎都是剖宫产,结果生产的时候大出血,子宫破裂......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印象比较深的,都是这样的病人,伊曼母亲的情况在当时来看甚至都不算特别难产。
但看到这篇报道,我确实蛮激动的。一想到我们当初剖宫产的孩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位产科医生,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服务了,觉得我们做的事非常有意义,很光荣也很自豪,这是援摩经历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酸甜苦辣的援摩生活
塔扎地处摩洛哥中北部山区,四周群山环抱,南面是撒哈拉沙漠。作为第一批中国医疗队,我们是抱着“打前站”的心态去的,当时医院给女士提供的宿舍是钢板打起来的简易双人间,男士则住了很长时间的会议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没有录音机和电视机,完全没有娱乐活动。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娱乐,因为当地的医生实在是太紧俏了,我和同事甚至连交接的机会都没有就成了这家医院唯一在岗的两位妇产科医生。病人又实在太多,我们俩每天24小时轮流值班犹嫌不够。其实摩洛哥有很多不错的风景名胜,但援摩的两年我除了去拉巴特公干(也是当天往返),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不过摩洛哥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如前所说,这里有许多上海见不到的病例,比如我在摩洛哥第一次见到了产妇破伤风,送来时苦笑面容、牙关紧闭等症状都出现了,好在治疗及时,最终救了回来。受环境所限,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新技能,比如手术室人力短缺,手术时没有洗手护士,全靠我们两位医师自己完成。有时候婴儿出来窒息,面色青紫没有哭声,我就充当儿科医生紧急抢救,等孩子安全了再交给护士。
在塔扎的那段时间,我们和当地医生护士处得也很融洽,去之前我们培训了三个月的法语,当地也有大使馆给我们开的语言课,再加上肢体语言,彼此日常交流毫无问题。护士常给我们介绍那里的风土人情,在看门诊时,也少不了她们的帮助,因为当地老百姓说的大多是阿拉伯语。
一起相处两年,中国医生的认真负责也感染着他们。我记得医院有一位当地的麻醉师,在唤醒病人时总是打耳光或者掐病人,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良习惯,一开始我们提醒了几次他也不买账。但后来的合作中,他被我们的专业精神打动,也逐渐改变了这一行为。
至今仍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团队精神。特别在妇产科,很多时候送来的病人情况很紧急,比如重度休克病人、重度感染病人等,我们会呼叫内科、外科、麻醉科等科室医生一起会诊,研究治疗方案,怎么给病人用药。对于这样额外的工作,队友们毫不计较,那种为了生命一齐努力的感觉,那么纯粹那么让人热血沸腾。
回国后,我们这个集体还被卫生部评为了先进医疗队。
那个年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不像现在,视频电话都很方便。在塔扎的生活,最难克服的恐怕就是思乡的情绪了。
那时和家里往来全靠信件,每个月集中送一次信到大使馆,错过了就要等到下一个月。到了寄信那天,前一晚哪怕忙到再晚,不睡觉也是要把信写好的。
送信的工作靠大家轮流。有一次,大使馆还给我们交代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原来,那里有一只德国犬,长得非常威武帅气,但它喜欢“沾花惹草”,所以想请我们帮忙做个绝育手术。于是,再去送信时我和骨科医师带上了麻醉剂和手术包,做了一回兽医,这也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兽医经历了。回国后还有朋友传回来消息,说是恢复得不错,我们也很欣慰。
回忆那两年,虽然很苦但也自有一番乐趣啊。
结语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我们去摩洛哥的初心使命,当我们回国时,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辜负身上的白衣,也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
如今我已经退休,来自远方的消息让我又再一次回到那里:过去的我们种下了一颗种子,如今这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结出了令人惊艳的果实。而我相信,一代代援摩医疗队员架起的中摩友谊之桥,还将继续见证新的感动,新的希望。
欢迎本市卫生健康工作者投稿,相关科普文章与视频等经所在科主任审阅后,投稿至单位宣传部门,经宣传部门提交“健康上海1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