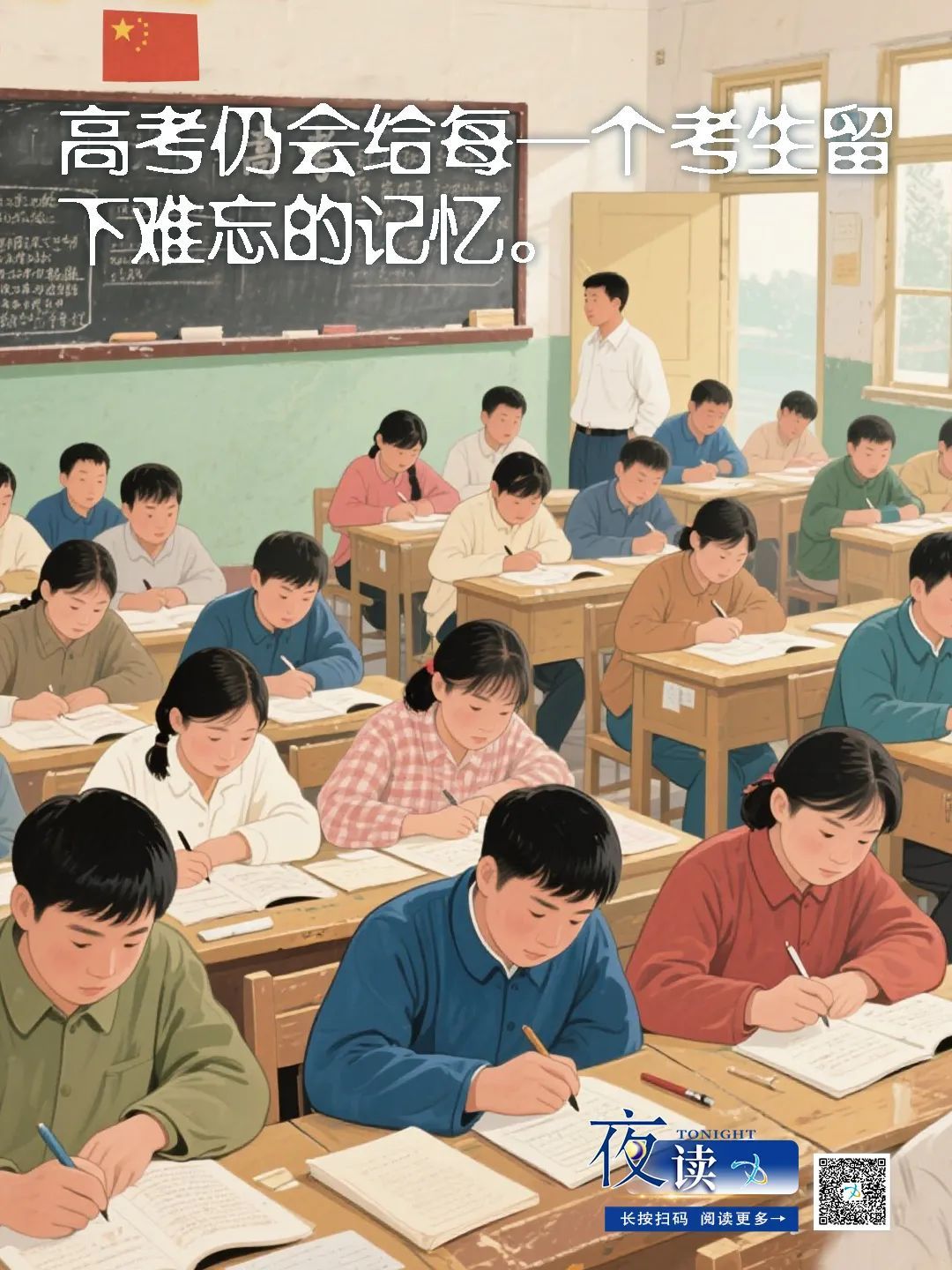
高考前后的期待,夹杂着的喜忧急虑愁,实在是五味杂陈。这滋味,40年前我经历过,至今难忘。
1977年10月21日晚8点,从当时最快捷的传播工具——广播里传来爆炸性的消息——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播音员那铿锵的声音,字字如重锤敲击着我的心灵。正在吃晚饭的我,端起饭碗捧菜碗,捧起菜碗端饭碗,不知到底该捧哪个碗。干脆,丢下饭碗,拉出箱子,翻检出当初带下乡的几本自认为用得上的书,连夜看起来。
插队已近10年,虽不必像刚来时那样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成了当地学校一员挑大梁的“代课教师”,但对前途的忧虑,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挂念,让一颗躁动的心,一直难以平复。现在,机遇降临,岂能错过?不搏一搏,岂能心甘?
谁知刚过两天,公社负责高考报名的工作人员特来传达口头通知:因超龄,失去报名资格。
如一盆冷水当头浇,我呆呆地站立在那里,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难道我此生就真的与大学无缘?几年来,紧闭的大学校门开了一条小缝,招收工农兵学员,“自愿报名,贫下中农推荐,领导审查,张榜公布”。现在,刚打开的透进希望之光的大门又戛然关上,重陷无望,何人能承受?
苦闷、彷徨中煎熬了两天,这个工作人员又登门传达“新精神”:老三届(1966、67、68年中学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后听人说,这并非新精神,只不过当初传达时他打了个瞌睡,听漏掉而已。虽在一刻值千金之时耽误了两天时间,但他两次登门的“负责”态度,我至今心存感激。
凭着重点中学的功底,插队期间没有完全丢掉书本的幸运,终于在千军万马中以高分挤过独木桥,获得体检资格。当年我们公社报名参加高考的有几百人,而达到体检线的只有3人。自然,我们的名气立刻传扬开了,虽极力抑制,暗喜已漾满心房。
1978年元旦,室外寒风瑟瑟,室内却热气腾腾,笔试过关的考生满怀着希望和憧憬,穿梭在体检的各个科室中。谁知在测血压的环节,我却突遭意外——被测到“血压高”。第二次测,更高了。在周围人投来的同情目光中,我呆呆地坐在一边,头脑里嗡嗡作响,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此时,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考生,默默地递给我两只他准备自用的、据说降血压有神效的冻柿子。在决定命运的第三次测量中,那个中年女医生轻轻地说:“合格。”霎时,刚才还感到刺耳的这个医生的声音是那么悦耳,看不顺眼的面容溢满了慈祥。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没弄明白,到底是那两个冻柿子真的有神效,还是“最后一搏”的淡定,抑或是那个女医生起了恻隐之心?
等待是难熬的,尤其是还有莫名的隐忧。虽说其时“阶级斗争为纲”已淡化,但考量“家庭出身”仍时不时会泛起白沫。“小业主”阶层虽不是斗争对象,但也不是依靠对象,仅仅是“团结”对象,至于团结到何种程度,那就全靠决策者的掌握了。
1978年3月下旬,各高校录取通知书逐渐发出。每天在校上课,虽望眼欲穿却表现得漫不经心,内心焦虑又谈笑如常,只是双眼总向校门口不停地瞟,脑海里设想着邮递员带来好消息时应该有的状态:要矜持,要大度,要若无其事,不要欣喜欲狂。
就在这无尽遐想中,迎来难忘的时刻。4月15日中午放学后,正饥肠辘辘地忙着煮饭,一名学生急匆匆奔至我家,气喘吁吁地说:“校长叫你赶紧到学校去。”此时还有什么要紧事?我顾不上熄灭灶膛里的火,跨上自行车,就直奔学校。平常10分钟的路程,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校门口已聚集了一群人,正围着校长看一张纸。我跳下车,顾不上跟周围的人打招呼,一把拿过,只看到“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我的双眼就模糊了,抬起头,举起双手,朝着蓝天,朝着白云,朝着远方的家,朝着日夜思念的亲人,喃喃地说:“迟到10年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啦。”什么矜持,什么大度,全跑得无影无踪。回到家,锅子里炒的韭菜已成了焦炭。
如今高考,已是“芙蓉国里尽朝晖”,虽不能人人都考进自己心仪的高校,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接受高等教育已不是太难的事,但高考仍会给每一个考生留下难忘的记忆。
投稿可发至zfk@yptimes.cn
作者 | 周彭庚
编辑 | 顾金华
诵读 | 田静
视觉 | 邱丽娜 刘晶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杨浦官方微信

(点击图片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