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图片回顾专栏往期内容

本期“办案心法”栏目“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特别专题,邀请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彭浩为我们分享域外法查明适用的“正确姿势”。
法律是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和准绳。因此,在依法适用域外法律的涉外案件中,能否准确查明、正确适用域外法,将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得到正确分配,直接关系到中外当事人的法律预期能否得到依法保护,直接关系到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良好形象能否有效树立。当前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域外法查明的目标定位不清晰、工作流程安排不科学、域外法查明适用质效有待提升等问题。近两年,笔者研习了上下级法院查明适用域外法的一些案例,也在一些复杂案件中反复探究查明适用域外法的有效方法,积累了些许心得体会。在此不揣肤浅,罗列数端,以飨交流。
明确查明目的:不止于查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而是要查明个案中直接可用的裁判规则
实践中,存在对域外法查明目的认识把握不够清晰的情况,认为“域外法查明”就是指查得与在办案件相关的域外法律规定,而与域外法的理解适用无关,并认为后者是中国法官的职权和自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认识进行域外法的理解适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委托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中外法律专家查明域外法,或者要求当事人提供域外法律时(以下统称查明主体),只是要求查明主体提供相关的域外法律规定,而未要求其提供有关法律应当如何理解适用的意见;有的案件在委托查明前未先行固定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也未要求查明主体针对个案情形查明与案件最相契合的法律,导致查明的域外法与案件具体场景脱节。这样的查明结果显然很难对个案中准确认定和正确适用域外法提供有效帮助。其后果,或者是不得不再次补充查明,严重影响涉外案件审判效率;或者是脱离域外法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法定的或通行的法律方法,完全按照法官的主观认识对域外法进行解释适用,极易造成域外法的错误理解适用。
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五条规定,查明主体提供的域外法律规定、判例等,都只是“域外法律的相关材料”。而域外法查明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查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在办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域外法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法定的或者通行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方法,找到能够直接适用于在办案件的具体裁判规则。我们知道,由于法律编纂体系化考量和立法技术等原因,各国的法律条文大多并非结构和内容完备的法律规范,在适用时需结合法律体系和其他相关条文将不完整的法律条文提炼转化为完整的法律规范。同时,考虑到法律普遍适用的需要,法律条文多为原则性较强的行为规范,而非可以直接指引个案裁判活动的裁判规范(裁判规则)。因此,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通过大量的解释工作,将不完备、不细化、不能直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完备、具体、契合个案情形的裁判规则,从而实现将法律规定适用于个案的裁判目的。域外法查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到某条或者某几条可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则。
明确域外法查明的最终目的在于查明个案中具体可用的裁判规则,而不止于查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对于准确定位域外法查明程序的目标任务、合理安排相关工作流程,及时、准确、高质量查明域外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由于域外法查明的最终目的在于适用,查明程序从一开始就要紧紧围绕查得能够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则这个目标而展开,不能脱离法律的个案适用进行抽象的域外法查明。这也要求法院在查明需求中,明确查明主体负有探明适用于具体个案的裁判规则的义务,而不满足于查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
第二,为确保域外法查明的针对性、有效性,应在启动查明程序前先行查清相关案件事实,固定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焦点,从而明确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并据此提出相应查明需求。
第三,为实现查明直接可用的裁判规则的目的,法官应将工作资源更多聚焦于在办案件中最需要清晰查明、有效澄清、准确阐明的争议问题上,在准确探明、充分论证可以直接适用个案的具体裁判规则上投入更多时间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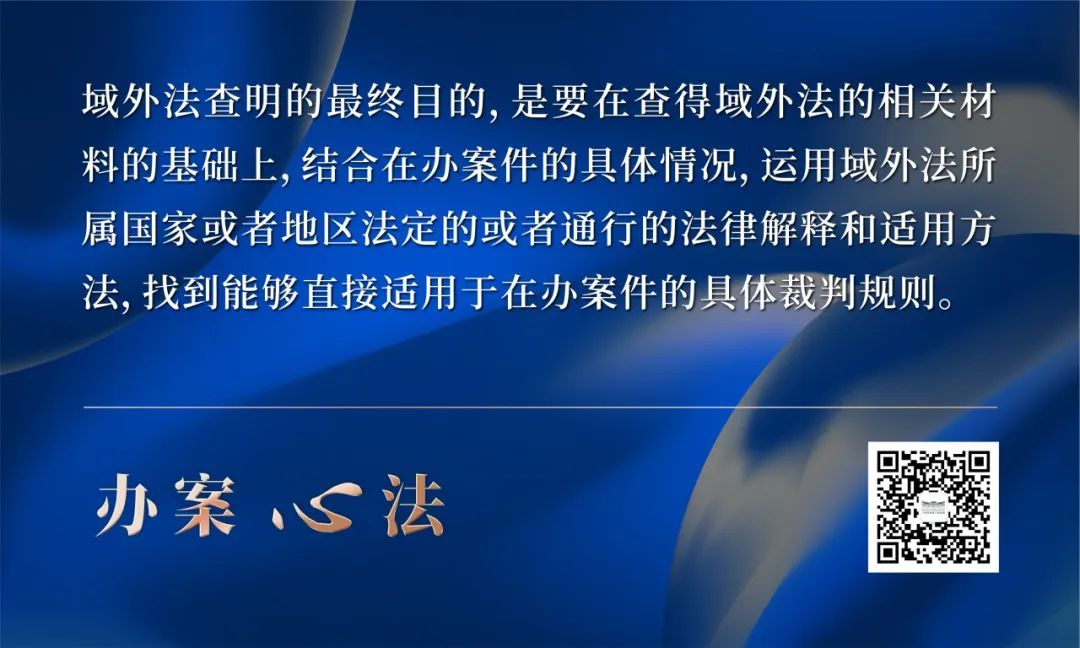
优化查明步骤:锁定目标,层层深入,确保域外法查明精准高效
聚焦“查明个案中直接可用的裁判规则”的目标,域外法查明就不能脱离个案进行抽象的法律查明,而是从一开始就要与在办案件紧密结合,做到“目光在事实与规范间的往返流转”。具体而言,要通过查清相关要件事实,固定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通过逐步缩小各方争议范围,固定域外法适用的争议焦点,精准锁定个案中需要查明域外法的具体范围,从而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效率和精准度。通过查明程序查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后,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关联性进行审慎审查,特别是要结合个案情况对域外法在个案中的可适用性作出准确认定,拨开法律与事实的重重迷雾,最终找到可以直接适用个案的具体裁判规则。
第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
为确保域外法查明的针对性,在启动查明程序前,应注意先查清与域外法适用相关的案件事实,并在委托查明材料中予以明确载明。这样可以先行固定个案中域外法适用的具体场景,让查明主体从一开始就紧密结合具体案情搜索相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到将有关域外法律适用于在办案件的合法性、关联性和有效性,提高查明工作的精准度。
第二步,固定争议焦点,精准锁定域外法的查明范围
在查清案涉事实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澄清和固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焦点。然后根据各方争议焦点,结合已知的域外法律的体系框架和各方当事人意见,逐步固定和提炼出在个案场景下需要查明的域外法的具体项目和需求。对此,以一个实际案例加以说明。
⁘ 案例1:原告与被告签订转让一家柬埔寨公司股权的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与全体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变更登记因故未完成,原告亦尚未实际参与柬埔寨公司经营管理。现双方当事人就原告是否已取得柬埔寨公司股东身份发生争议,相应的域外法查明需求如何提出较为妥当?
分析:根据国内案件审判实践可以发现,“股权转让自何时完成”虽然最终落脚为一项法律判断,但往往会涉及对一系列涉案事实的综合分析与评判。因此,如果仅以“柬埔寨关于股权变更条件和时点的法律规定”之类的抽象问题作为查明需求,很可能会出现查明主体提供的法律规定不能准确地适用于个案的问题。因此,建议在委托查明材料中要详细载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于域外法适用的意见和争议焦点,要求查明主体针对个案具体情形提供相关的域外法律规定,并就相关法律规定如何适用于个案提出分析论证意见。
第三步,启动查明程序,对查得的材料依法进行审查
在明确查明需求后,就可以运用法律规定的途径,正式启动域外法查明程序。经过查明程序取得域外法的相关材料后,即须以适当程序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对相关材料载明的域外法律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关联性作出认定。其中,对于域外法律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的审查,只需对照相关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规定的实际情况加以“抽象的”审查即可。而对“关联性”的认定则必须对域外法律能否适用于具体个案作出判断,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域外法律在个案如何理解适用的关键问题。
为确保域外法律认定及适用的程序正当性和实体正确性,必须充分发挥正当程序的支撑保障作用。一方面,查得的相关材料均应在法庭上出示,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如有必要,可以通知查明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出庭接受询问,通过充分听取他们的专业分析意见,帮助法院作出准确判断。
第四步,综合分析判断,准确认定域外法的内容及其理解适用
经过域外法律提供、质证、询问等一系列程序后,最终还必须落脚在对域外法的准确认定和正确适用上。关于域外法认定的标准,《解释(二)》第八条已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审理中,法官可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准确判断。需要强调的仅在于,依据现行法律及“法官知法”的古老法谚,法官对于查明适用域外法负有严格的法律责任,应当尽最大努力、采用适当途径准确查明域外法,而不能浅尝辄止、轻易认定“不能查明域外法”。
第一,根据《解释(二)》第二条第二款,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中一项途径无法获得域外法律或者获得的域外法律的内容不明确、不充分的,应当通过其他适当的途径作进一步补充查明,而不能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
第二,根据《解释(二)》第八条第二项,域外法查明结果出来后,如果当事人对其内容及理解与适用提出合理异议,或者确有必要的,应当补充查明,并在综合分析、比较、甄选后作出审慎认定。换言之,不能仅以当事人对域外法的内容及其理解适用存在异议为由,直接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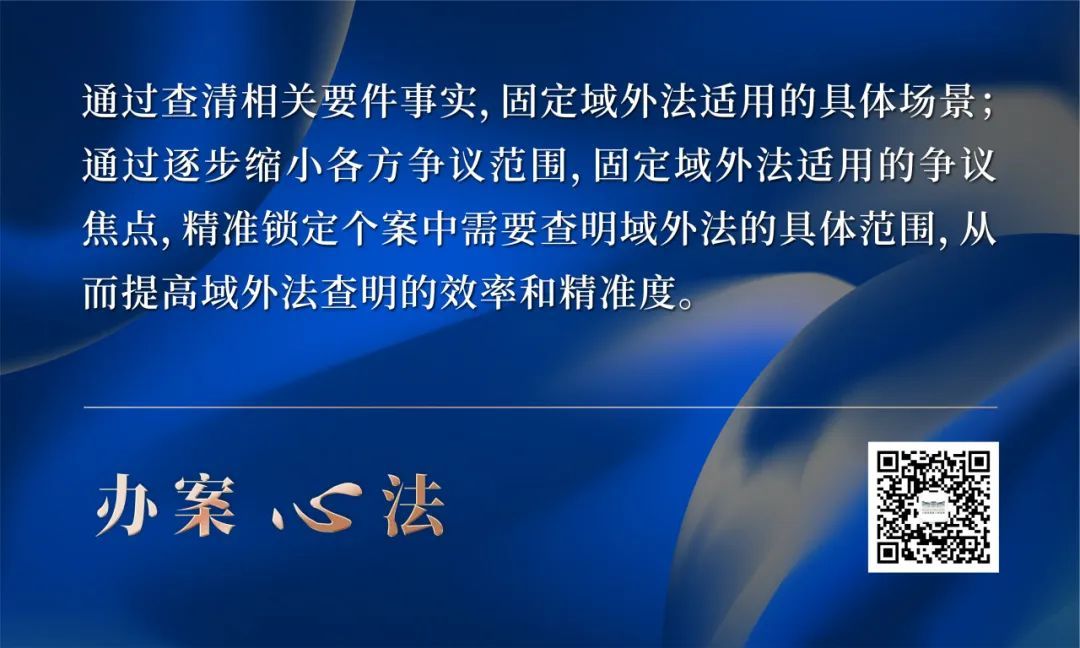
关注法律适用方法:努力做到“如同外国法官那样解释和适用外国法”
将域外法适用于在办的具体案件,势必涉及对域外法律规则内涵、外延的解释与具体运用。从保护中外当事人对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的合理预期出发,域外法适用的理想状态是,中国法官要如同外国法官审理该案那样,运用域外法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法定的或者通行的法律方法去解释和适用域外法,并据此作出正确裁判。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在加强涉外法治的时代背景下,涉外法官有责任朝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尽可能地趋近于这个目标。
(一)将案涉争议放到域外法律体系的正确位置
由于长期在中国法律的体系框架内思考法律适用问题,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容易出现不假思索“自动套用”这个体系框架的问题。但同一法律问题在不同法域的法律体系框架内所处位置往往会存在很大区别。为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在适用域外法时,有必要暂时“屏蔽”已经习惯了的中国法律体系框架,以未知心态去探明案涉争议问题在域外法律体系中的正确位置,并根据与其最相契合的域外法律作出裁判。为说明这一问题,也举一个实际案例。
⁘ 案例2:自2017年起,某中国公司每年向某奥地利公司发送合同订单,奥地利公司每次均给予书面承诺,但在回函中均载明双方权利义务应受回函附件所列“一般交易条件”约束。中国公司对回函及附件予以接受并按约履行义务。后双方发生纠纷,奥地利公司提出回函附件系其提出的新的要约,中国公司未在合理期间作出承诺,故双方就附件未成立合同关系。
分析:关于上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是否已就附件成立合同关系,如适用中国法律,可以根据民法典关于合同形式瑕疵的履行治愈规则、交易习惯、诚信原则等相关规定加以认定。相应法律规定在奥地利民法典框架内也均存在。但认真研读奥地利民法典关于合同成立的全部规定后可以发现,奥地利民法典上还有一条与该案争议更相契合的法律规定,即第864a条。该条法律对“一般交易条件”(类似于中国法律上的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基于法律适用准确性的要求,该条款才是该案应予适用的法律依据。
(二)审查域外法律与案涉争议是否契合
这个问题在适用普通法特别是其判例法的案件中更加突显。普通法系的法院在适用判例法时,需按照一套复杂的机制和方法,对在办案件与判例的相似性进行严格比对,以确保先前的判例可以准确地适用于在办案件。因此,在依法适用判例法的案件中,有必要参考该法域的法律适用机制和方法,对查明的域外法能否适用于在办案件进行必要的探讨。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查明机构或者法律专家的智力优势,或者通知域外法所属法域的专业人士到庭陈述意见甚至开展辩论,帮助法院正确适用相关判例法。
(三)遵循域外法律体系通用的法律方法
查得域外的法律规定后,还必须配合运用其所属法律体系的法律解释与适用方法,才能得出该域外法律规则的准确含义。比如,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明文规定仲裁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稍作探究即可发现,几乎没有两个国家对于“书面形式”的理解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解释和适用域外法律时,也要尽量“忘却”中国法律的语境和解释方法,尽可能地将查得的域外法律还原到其“母国”的法律体系和文化语境下,按照该法域法定的或者通用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方法进行解释适用。由于涉外法官不可能是所有域外法的专家,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更多依赖查明机构或者法律专家的协助,同时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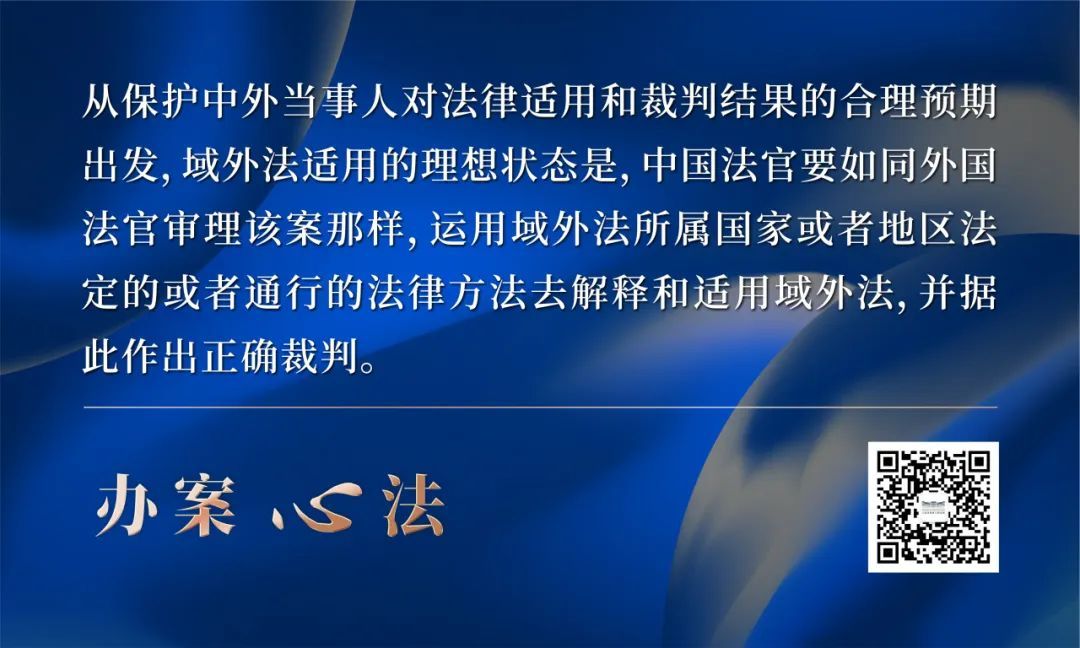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复杂,司法实践中涉及域外法查明适用的案件越来越多。能否准确查明、正确适用域外法,已经成为衡量涉外司法质量的重要“试金石”。相应地,域外法的查明适用应当成为涉外法治人才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之一。促进域外法的准确查明适用不仅需要完善制度机制,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专门力量的智慧优势,更呼唤涉外审判人员及时总结一线审判经验,加强理论研究和深度思考,提炼形成更多务实高效的实践方法。期盼本文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仁参与探讨,在思想交锋中积累真知灼见,促推涉外司法实践发展。
作者介绍
彭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博士研究生,现任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获评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实务专家,“上海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家”等,上海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成员。主审的1起案件入选全国法院指导性案例(第201号),2起案件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3起案件入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参考性案例,多起案件获评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全国法院优秀案例评选二等奖、上海法院十大优秀裁判文书等。参与执笔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重大调研课题、上海法院重大调研课题、上海司法智库调研课题等10余项。在《法律适用》《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1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次荣获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征文二等奖、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二等奖等奖项。
高院供稿部门丨干培处
作者:彭浩
责任编辑:孟文娟、王英鸽
编辑:左雨欣
声明丨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高院”公众号
▴ 点击上方卡片关注“上海高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