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十九批法答网“精选答问”共6个( 点击查看详情),上海法院3则答问入选。
前期,上海法院已有5则答问和4则提问入选法答网“精选答问”。
答问一主要围绕“在舆论监督中肖像权的合理使用如何认定?”进行了解答,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周浦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季佳彬提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上海法院民事条线调研骨干)纪学鹏答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奚少君审核。

问题
在舆论监督中肖像权的合理使用如何认定?
答疑意见
舆论监督中合理使用肖像权涉及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条、第一千零二十条第二项、第五项的适用。一般认为,适用舆论监督合理使用肖像权应当满足两个要件:一是目的的公益性,即对肖像权的制作、公开、使用,是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所必须的。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施某某、张某某、桂某某诉徐某某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2015〕江宁少民初字第7号)的裁判要旨即认为,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揭露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发帖人在其微博中发表未成年人受伤害信息,使用了施某某受伤的九张照片(使用时已经对脸部作了模糊处理),所发微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基本一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不应认定此行为构成侵权。二是手段的相当性,即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所制作、使用、公开的肖像应当具有合法来源。比如,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新闻采访应当符合相应准则,不得以非法侵入等不当方式侵扰权利人的生活安宁。同时,在使用当事人的肖像时已经采取了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比如,在舆论监督不可避免使用未成年人肖像时,就有必要通过打马赛克等方式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进一步保护。此外,对合理使用的认定,还需要结合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综合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
答问二主要围绕“视频网络平台经营者收集用户的登录、观影记录信息是否属于侵犯用户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权益?”进行了解答,由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助理李傲然提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上海法院民事条线调研骨干、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干部)曹湘芹答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程小勇审核。

问题
视频网络平台经营者收集用户的登录、观影记录信息是否属于侵犯用户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权益?
答疑意见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虽然法律未明确列举网站登录信息、观影信息是否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客体,但是上述信息明显具有与个人喜好密切相关的可识别性,对视频网络平台而言则具有营销价值。比如,很多视频网络平台可以通过观影记录计算会员偏好,从而不断推送类似视频,赚取更多流量广告收益。而且,视频平台也普遍在个人用户隐私界面设置其他人对观影记录可见或者不可见选项供用户勾选,这说明视频平台的经营者也认为观影记录具有私密性。综上,认定视频平台用户登录信息和观影记录为个人信息进而加以保护,具有合理合法性。
在用户注册会员时,视频平台的经营者通常会告知将收集用户登录记录和浏览观影记录;而作为一般用户,对平台收集自己的登录记录和浏览观影记录也是明知的。故在平台已明确告知并获得用户同意的情形下,收集该记录通常并不构成侵权。但是,视频平台作为个人信息的收集人,对相应信息的使用应当以合法、正当、必要为边界,并遵循诚信原则,否则仍然可能成立侵权。
答问三主要围绕“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誉权侵权责任应当如何认定?”进行了解答,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助理陈力夫提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上海法院民事条线调研骨干、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干部)曹湘芹答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成阳审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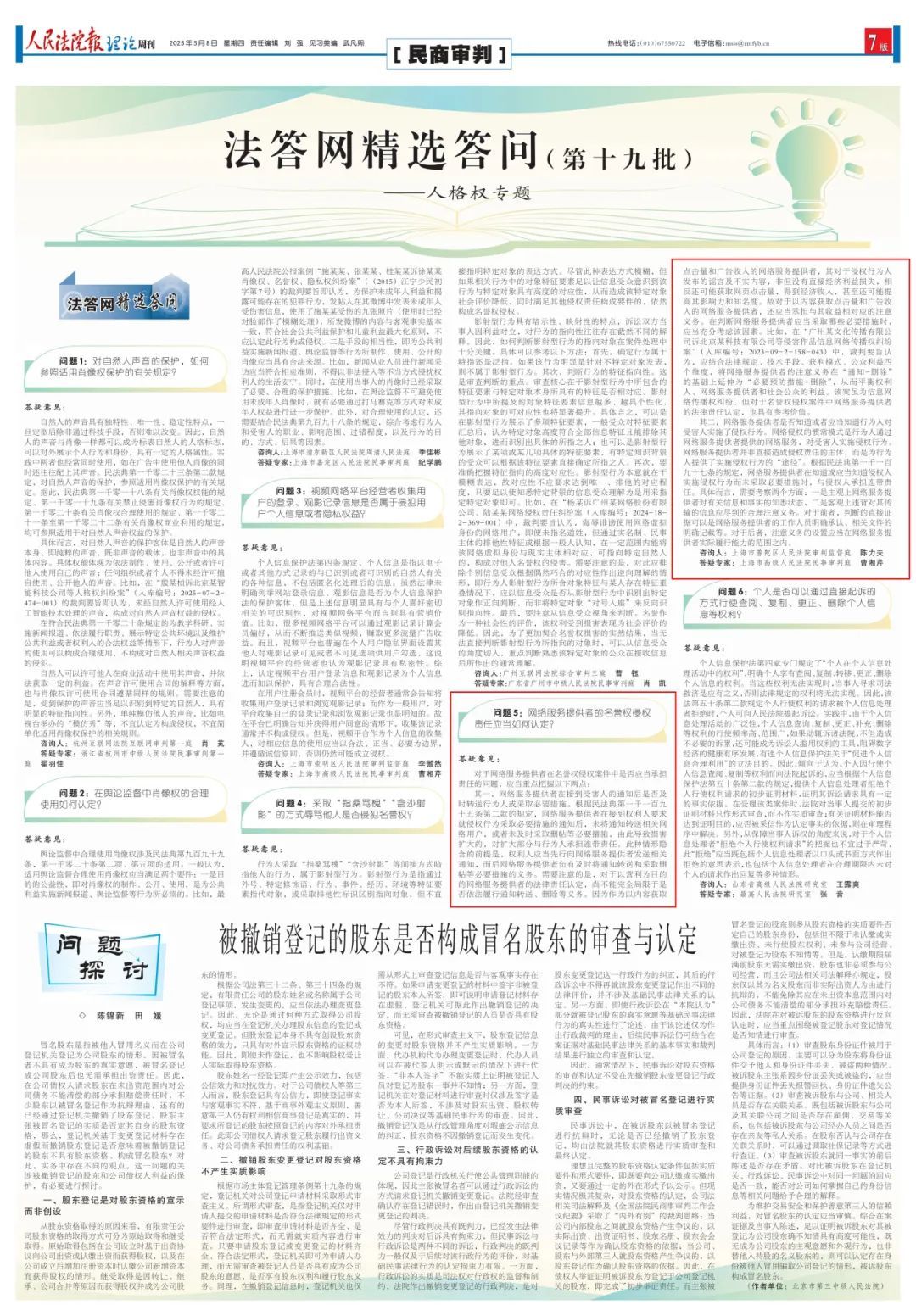
问题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誉权侵权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答疑意见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应当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其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受害人的通知后是否及时转送行为人或采取必要措施。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要求就侵权行为采取必要措施的通知后,未将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或者未及时采取删帖等必要措施,由此导致损害扩大的,对扩大部分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此种情形隐含的前提是,权利人应当先行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送相关通知,而后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及时将通知转送和采取删帖等必要措施的义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认定,尚不能完全局限于是否依法履行通知转送、删除等义务。因为作为以内容获取点击量和广告收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对于侵权行为人发布的谣言及不实内容,非但没有直接经济利益损失,相反还可能获取网页点击量,得到经济收入,甚至还可能提高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故对于以内容获取点击量和广告收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当承担与其收益相对应的注意义务。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时,应当充分考虑该因素。比如,在“广州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9-2-158-043)中,裁判要旨认为,应结合法律规定、技术手段、获利模式、公众利益四个维度,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在“通知-删除”的基础上延伸为“必要预防措施+删除”,从而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该案虽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但对于名誉权侵权案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认定,也具有参考价值。
其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对受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网络侵权的惯常模式是行为人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网络服务,对受害人实施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非直接造成侵权责任的主体,而是为行为人提供了实施侵权行为的“途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而言,需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有关信息和事实的知悉状态,二是客观上违背对其传输的信息应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对于前者,判断的直接证据可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工作人员明确承认、相关文件的明确记载等。对于后者,注意义务的设置应当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履行能力的范围之内。
高院供稿部门丨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蒋梦娴
编辑:孙小敏
声明丨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高院”公众号
▴ 点击上方卡片关注“上海高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