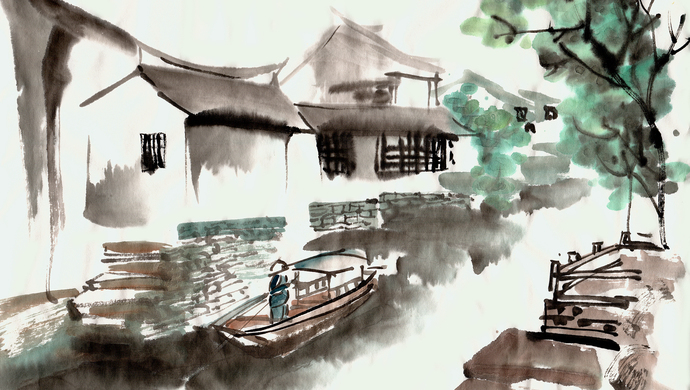
不用担心各大景点人山人海寸步难移,不必为了省钱买一趟红眼航班,不会有人塞给你一张长长的清单叫你帮忙代购,也不会有被堵车支配的恐惧。排除所有这些令人扫兴的因素,给你数十日的空闲时光,为你安排一场江南之行,你会怎么玩?
一百多年前,寓居沪上的英国人葛骆(William R. Kahler)早就写好了旅行攻略。一本《环沪漫记》(Rambles round Shanghai),一本《中国假日行》(My Holidays in China),均收录在上海通志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主编的《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中。前者所涉及的地界主要以上海为中心,辐射至上海郊县以及苏州、杭州、嘉兴等周边城市,旅途中的风景、习俗、传说、民情等见闻各自成篇。而《中国假日行》则介绍了三条完整连贯的线路,涉及的范围也更远、更广。
葛骆说:“在中国度假的最令人愉快的方式就是雇一艘游船航行。”就让我们跟随他一百多年前的足迹度个假,看看那时江南的世情百态。
外国人也喜欢掉书袋
出发之前,我们不妨再多了解一下这位“导游”。
关于葛骆的生平记载虽然不多,但他在中国的经历之丰富,仅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已可见一斑。1859年,尚在幼年的葛骆来到中国,自此与这片土结下了长达数十年的不解之缘。1879年,他在九江新关担任三等钤子手;1897年,《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葛骆来信上,他的署名头衔已是虹口第二救火队领班救火员;1903-1904年,他又连续当选工部局火政处的总机师。不仅如此,在租界重要机构担任负责人的葛骆先生,于当时的新闻界也颇有名声——他创办并主编过一份戒酒会刊物《戒酒新闻纸》(Temperance Union),《中国假日行》即由该社出版,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可以想见,这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将“跨界”玩得风生水起的葛骆先生,定然是朋友圈里爱攒局、能张罗、会来事儿的一号人物。
《中国假日行》中的前两次旅行都是从黄浦江雇船出发,经苏州河,沿江南内河行进:第一次旅行是在1887年10月,途径川沙、七宝、泗泾、松江、嘉兴、杭州、绍兴、余姚等地,最后至宁波返回;第二次是从上海到溧阳,途径苏州、江阴、无锡、宜兴、常州。而第三次,葛骆和朋友们从九江到芜湖,一路乘游艇游长江,这样的旅行体验,让现代人听起来也多少有些艳羡。
明末文学家张岱在其《夜航船》的序言中就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船上的乘客涵盖三百六十行,谈话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前一刻夸夸其谈,后一刻兴许就哑口无言。葛骆自幼在来华,对中国轶事典故所知甚多,和夜航船上的人一样,他在航行途中也时常喜欢抖落抖落自己肚子里的存货。
在七宝的水边有人放鸭,葛骆便随即联想到一个关于鸭子的故事:从前有个人偷了邻居的鸭子来吃,夜晚,浑身长出鸭毛。梦中有人告诉他,此乃上天的惩罚,需要失主痛骂他一顿,鸭毛才能脱落。此人几次绕着弯子想让邻居开骂,谁知邻居雅量,从不骂人。偷鸭人只好将自己的遭遇如实相告,邻居这才将其痛斥一顿,偷鸭人果然立刻痊愈了。熟悉明清文学的人不难发现,这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骂鸭》。文言小说中的故事都能信手拈来,说葛骆是位“中国通”也不为过了。
葛骆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经常会下意识地和西方故事进行对比。在松江的东岳庙,葛骆向读者介绍“东岳大帝是东方的冥王哈德斯”。而在徐家汇博物院,葛骆竟能从院长韩伯禄神父关于鳄鱼的研究课题上,联想到韩愈在广东撰文驱逐鳄鱼的典故,并称韩愈是“中国的圣帕特里克”。葛骆在写游记时,心中想象的读者大约都是西方人,书中的这些类比显然是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的理解。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眼里,这倒也不失为一种趣味。
也许是道听途说的版本太多,也许是西式思维理解有误,也有可能是书写成文时忍不住想添油加醋,总之,一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到了葛骆那里会有些变形。比如,“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地被葛骆平移到苏州和松江,他还为男女主人公在松江的一座花园里安排了一场浪漫的偶遇。在葛骆笔下,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民间传说中更通行的名字是“范喜良”)也并非因修筑长城而死,而是因为秦始皇不愿意为修长城牺牲千万条人命,便依照占星家之言,杀万喜良一人来抵千万人的性命(因为他姓“万”)。城门护卫被孟姜女寻夫之事所打动,破例为她打开城门,葛骆借题发挥:“在中国,涉及金钱和感情的事件,感情更为重要。”
张岱的夜航船上,夸夸其言的士子因常识错误而被同宿的僧人取笑,不得不让蜷缩着的僧人伸伸脚。葛骆在船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也不知有没有同行之人就其讹误之处争辩一番,然后叫他让个位置伸伸脚呢?
巨变时代的江南民间信仰
近代以来,江南,尤其是上海地区,逐渐形成华洋杂处、东西兼容的社会形态,渗透公共领域的各大宗教亦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葛骆行经许多庙观、祠堂、教会,我们从中亦可对近代江南的宗教生活稍作管窥。
在泗泾的圣巴塞洛缪教堂,葛骆观看了一场弥撒。这里的教众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妇女坐在右边,而男子坐在左边,女孩和男孩们则紧挨着祭坛的护栏分列两边,正厅中央被一位上层社会出身的女子单独占据着。”一男子唱诗时犯了个小错误,旁边的人随即笑出声来,进而开始捧腹大笑。这样的场景太不严肃,葛骆隐隐透着不满。他也并不认为中国人能够真正理解天主教教义,他直言:“也许罗马天主教没有起到其他什么作用,可至少他们教会了中国人干净和整洁。”不过,中国天主教徒的整洁和体面倒是给葛骆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佘山顶上的圣母堂参观时,他也发表过类似的议论。
在葛骆的记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宗教信仰的混杂(抑或是一直都很混杂?)。在苏州城宝带桥武庙,葛骆等人结识了一位文星方丈,方丈盛情邀请他们来庙里参观。武庙固然应当供奉关帝,可这座庙里还供奉着许多其他神像,比如道教的财神像、佛教的因陀罗像。而这里的信徒对清规戒律似乎也没那么严肃,葛骆就惊讶地发现文星方丈的晚饭疑似是肉。
江南很多盛极一时的寺庙,到了清末逐渐破落,加上时局动乱,便再无人问津。譬如南翔的万安寺。这座落成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的古寺曾是一方形胜,与南翔寺、万寿寺并称“南翔三大寺庙”。数百年沧海桑田,万安寺几经起落。在与葛骆年代最接近的《光绪嘉定县志》记载到万安寺当时的情况,仅有“今废”二字供人凭吊。因何而“废”?又“废”到何等程度?志书并无记载,而葛骆通过他的游记将更多的信息告诉了后人。从上海到溧阳的旅行中,葛骆和朋友们途经南翔,看到万安寺一片荒凉——屋顶多处漏洞,前殿住满乞丐,大大小小的佛像残破不全,仅剩一尊农神还算完好。他们从乡人口中得知,这些都是太平军劫掠的结果。葛骆还信笔提了一句,万安寺的前门上写着“四季安乐”。满目疮痍之下,这四个字倒像是有几分“乐景写哀”的悲凉。
舌尖上的江南
美食,是对赶路人最熨帖的犒赏和慰藉。对一个旅行家而言,“会吃”是和“会玩”同等重要的素质。就像葛骆一行从上海到溧阳,还不忘带上一位手艺精湛的华人主厨。不过,江南物产丰饶,从不缺少大自然的馈赠,即便带着厨子旅行,他们也从未错过品尝当地的美味。
饭稻羹鱼的江南,最讲究食材的新鲜。葛骆显然是深谙此理,他对捕获水产的方式表现得兴致盎然。最常见的是撒网捕捞,葛骆船行太湖时随时经常看到湖边有很多张开的渔网,网里还有很多巧妙串联在一起的砖坯,用以增加渔网的吃重。也有用大网来捕鱼的,渔民们会花费七八个月的时间,拼织一张巨大的渔网,将它和绞盘以及几根粗大的竹竿相连。这种装置很巧妙。一边的河岸上垂直竖起一根的竹竿,然后将一根长绳的一端系在竹竿顶部,另一端系在大网的一只角上。大网的另一只角与另一根竹竿相连,这根竹竿一头连在岸上,当大网下沉,竹竿的另一头沉入水里。两个绞盘在河的另一边,用绳子把绞盘和大网的其它角相连。绞盘绞动就可以将绳子拉紧,大网就被拉出水面。船只朝着网的方向推进,落网之鱼就被移到了船上。
大网捕鱼考验的是渔民们团结配合的默契程度,而夜间的捕捞工作,则最能体现中国人为美食而发散的智慧。在渔船的一边船舷上系一条约2英尺高的直立的渔网,另一边船舷放一块与船同长、约3英尺宽的白漆板。当船桨在水中搅动,受惊的鱼儿以为光亮的白板处是安全所在,便直挺挺地冲撞过来,结果一个个掉到船上。这时,眼疾手快的渔夫迅速用另一边的渔网罩上,以防鱼儿逃脱。若是运气好,哪怕渔夫在船上闷头大睡,也能满载而归。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鱼虾以外,其他水生的动植物,同样是常见的江南美食。比如菱角、田鸡、甲鱼,葛骆对这些食物的获取方式同样津津乐道,可见这群高端玩家一路上从未亏待自己味蕾。
中国人吃饭的场景,在葛骆笔下亦是妙趣横生。他们来到溧阳一家本地餐馆,一顿饭就吃得非常“接地气”。这家店生意很好,烧出来的食物也令人食指大动——“很多盘碟排成一列,有肉馅和甜馅的汤团,有捣碎的豆子和酱汁,有鸡、鸭以及其他禽类的肉片,还有很多或煮、或盐拌、或生吃的蔬菜及挂在钩子上的烤鸭。”不过葛骆也没忘了抱怨一句“这些都被放在店外面,无遮无挡,根本不介意四处飞扬的尘土”。最具市井气的是店里的顾客:“有些人忙着猜拳,每个人都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同时灌醉边上的人。随着游戏的进行,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的脸也越来越红,这是因为和烈酒能让本地人满面红光。楼下有个人坐在桌边,用含糊的声音吆喝着从楼上传来的各种指令……”这样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大约也是中国式饭桌留给外国人的典型印象。
有瓦肆勾栏间的人间烟火,自然也有大雅之堂上的玉粒金莼。在无锡,一位银行家在高级游船上设宴款待葛骆一行。除了寻常的鸡鸭鱼肉,席上更有鸽子蛋、鱼翅、燕窝、海蛞蝓这些美馔珍馐。中国人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充分体现在摆盘和食器的讲究,各种杂食被切成小片、排成一列,每份菜肴都放在小小的盘子或者浅碟上。主人亦很热情,经常帮忙夹菜,但葛骆对此有些嫌弃:“主人为了显示他的好客,把筷子放在自己的嘴里之后,他又用自己的筷子夹了很多好吃的,放在我们的碟子里。”
一个“中国通”的傲慢与偏见
葛骆毕竟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行走中国社会的许多“规矩”,他都清楚得很。比如在溧阳的城隍庙里,道士巧妙暗示葛骆要给写香油钱,他立马心领神会,并且在书中不无得意地告诉读者:“就算他不说,再过几分钟我们也会给的。”
然而,就像不堪忍受餐厅的喧闹和歌女的伴唱一样,虽然葛骆算得上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但在字里行间依旧流露出对华人社会难以适应的矫情。
在杭州坐轿子,对于葛骆来说就不是一次舒适的体验。他在书中首先介绍了轿子的三六九等:“官员和有钱人坐头等轿,我们打算坐二等轿,至于三等轿则被官员的随从全部包走了。”他感叹轿子是一种相当别扭的发明,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座位太低。而杭州的大部分街道又很狭窄,轿夫穿街走巷时,拐弯转角都非常困难。
如果说乘坐轿子让葛骆觉得有些别扭,那观看地方戏曲的经历对他而言简直就可以用“糟糕”来形容了。有一次偶遇村里的巡回戏班在表演,葛骆坦言:“如果你的神经承受能力还算正常,那么这种表演你只要看过一次就应该觉得够了。”锣声鼓点在葛骆听来嘈杂难耐,演员们的唱念做打在他眼里好似群魔乱舞,简陋抽象的戏台布景简直是在考验人们的想象力,而观众们的喝彩叫好声传到他耳朵里就是此起彼伏的噪音。葛骆觉得中国戏曲很难翻译的原因是“它们太粗俗了”。这样的评价未免以偏概全——很多地方戏缘起于农村生活,难免有其粗俗之处,可但凡经过改造后登堂入室的戏曲大多唱词优雅。况且,中国地方戏曲品类繁多,葛骆所见的乡村社戏不知是什么曲种,轻易便将难以翻译归因于“粗俗”二字,实是有些武断。
葛骆也感觉到了江南大地上蓄势待发的力量,可他依旧端着代表“先进文明”的姿态发表评议:“中国正随着时代的需要觉醒,而且朝着外国人希望它能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发展着。”今天的中国当然不是依循着一百年多前外国人的意愿发展而来,我们应当坚信,一国之文明有其属于自己的生命。
虽然葛骆对中国社会时常表现出西方人特有的优越感,但书中有句话倒说得公允:“就算外国人在中国人当中待一辈子,对他们的了解也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
结语
明清以降,江南一带就是涉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上海自1843年开埠伊始,更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汇聚了数量可观的外国人。今天,我们有幸能够通过多近代上海外文文献了解这一特殊的群体,了解他们在一个刚刚“睁眼看世界”中国,是如何看待这片“开风气之先”的土地。他们既是江南集体记忆的重要构建者,亦是江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一百多年前的葛骆站苏州河畔,看到两岸的一派新兴景象——“沿河北岸设有从上海到苏州的电报线,它还将从北到南延伸到整个中国。有四条电话线额而下,直达苏州,过了苏州之后,还有三条线继续沿着大运河向前伸展着。”
在那样一个蒙昧与觉醒之间的时代,酝酿在江南的蓬勃希望,就像这些线路一样,向着更远的地方不断延伸,直到今日,依然伸向无尽的未来。
 我也说两句
我也说两句
























































